皮肤炭疽病的症状图片,什么是炭疽细菌?
讲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真实版生化危机:前苏联制造的剧毒之岛,来解读一下炭疽细菌的可怖!
在《生化危机3》的结局,政府为了遏制浣熊镇的那场可怕事故,最终选择的方案是用一枚核弹彻底毁灭了这个城市。然而在现实里,这种办法可能并不一定真的像游戏中那么简单有效,一了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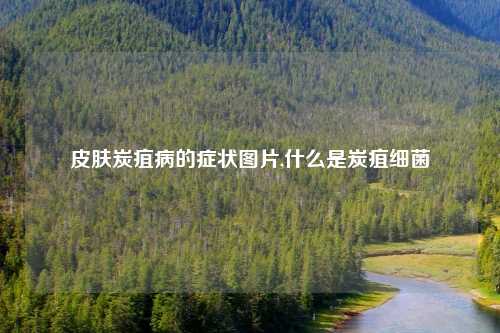
今天想说的,就是发生在前苏联的真实版生化危机,它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可能很多人有所耳闻;至于第二个部分,知道的恐怕就少一些了。
01
1979年4月的一天,前苏联工业重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Sverdlovsk,现名叶卡捷琳娜堡)的24号医院里,忽然送来了三位症状相似的病人,他们都表现为发高烧、头痛胸闷、喘不过气。
接手这几位病人的,是24号医院呼吸科的主治大夫玛格丽特·伊莉延科(Margarita Ilyenko)。她一开始以为是肺炎症状,但很快发现病人的病情恶化比他想象得要迅速得多。刚刚第二天凌晨,三位病人中就有两名已经死亡了,剩下的一名也奄奄一息:他的口鼻不断溢出渗血的黏液,因为呼吸极度困难已经陷入了昏迷。
就在第二天,城市中另一家20号医院里,也出现了同样的事情。
“我们这儿有几个病人很不对劲,高烧不退,一直剧烈咳嗽,还不断呕吐……”20号医院的呼吸科主治大夫雅科夫·克利普尼策尔(Yakov Klipnitzer)通过电话向伊莉延科焦虑地讨论病情。
“我们这里也是,一天之内大厅里就挤满了病人,病床上到处都是打着寒颤的人,很多病人的皮肤上都长出了黑色的水泡,看起来很恐怖。”伊莉延科回应道。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某种传染病吗……”
医生们的猜测并没有错,这些病人们的确感染了什么,只是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类似的病例,也不知道该如何医治。
短短一天之内,死亡人数就急剧上升到数十名,很快24号医院的停尸房里已经堆满了尸体,死神在这座中型城市里肆虐着……所有市民都开始惶恐起来,但却不知道这瘟疫是从何而起。
通过整理病人的档案,伊莉延科发现了病人们的某种共性:他们似乎都来自于城市32区,也就是奇卡洛夫斯基区的一家陶瓷厂。难道这家陶瓷厂内存在某种感染源吗?
此刻的陶瓷厂,已经暂时封闭。身穿严密防护服的疾控中心主任维克托·罗曼诺科(Viktor Romanenko)正在安排消毒人员不停地用氯气喷洒消毒。如果陶瓷厂正常工作时,可以透过厂房巨大的窗户,看见工厂内部挤满了上百名忙忙碌碌的工人。
很快,政府对外公布了结论,这是因为陶瓷厂工人们集体食用了某私人屠宰场贩卖的,被污染的肉类,才导致的瘟疫死亡事件。
“他们纯粹在胡扯,”在这家厂子上班的尼古拉·布米斯特罗夫(Nikolai Burmistrov)根本不相信这种解释,“我们很多人也吃了他们家的肉,为啥我们都没事?”
工人们的质疑是完全有道理的,特别是结合当时苏联的国际环境,再考虑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城市定位,就不难猜测到,政府一定在隐瞒着某种可怕的真相……
02
自从二战开始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就一直是苏联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生产中心。在这里,每年都有大量坦克,核武器和其他军备被制造出来。
陶瓷厂所在的32区,就有着一座军事基地,并驻扎着两个坦克师。紧挨着32区的19区(Compound 19),看起来更加神秘,这里矗立着一座戒备森严的军事设施,然而仅仅从外形上看,似乎只是个寻常化工厂的样子。
在那个年代,根本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座“化工厂”究竟在制造什么东西——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生命体。
1945年,当苏联军队占领了伪满洲地区时,他们找到了日本那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所建立的生化实验室。在实验室的遗留品中,苏联人发现了一种可以作为生物武器的材料:炭疽。当年,惨无人道的日本人抓了大量中国人,在此进行炭疽活体实验,并留下了多份报告。
于是,苏联人不动声色地将所有炭疽样本和研究报告全部移走,偷偷带回自家研究。是的,他们特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建造了一座秘密实验基地,专门研究各种生化武器,也就是19区的这一座。
那么,炭疽是怎样从这座生化基地,传播到了陶瓷厂的呢?
从感染者的分布区域图上,我们可以觅到一些蛛丝马迹:
病人们的分布,明显呈现出一种从某个点开始,向着东南方向不断扩散延伸的狭长扇形。是的,这个点就是19区生化实验基地。
引用后来负责调查此事件的哈佛生物学教授马修·梅塞尔逊(Matthew Meselson)的说法就是:“工人们吃肉并不会造成50公里内直线型区域感染的分布形状,只有风可以做到这一点”。他的妻子珍妮·吉列(Jeanne Guillemin)同样参与了此事件调查,并在1999年发布了一本专门介绍此事件的书:《炭疽:致命疫情的调查》(Anthrax: The Investigation of a Deadly Outbreak)。书中提到不仅仅是工人和市民,当地还有很多牲畜也同样感染了炭疽。
再结合当天的天气情况,当时风向正是朝着陶瓷厂刮过去,那么传播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如此一来剩下的谜团只有一个:为什么炭疽会从19区的生化实验室里泄露出来?
直到许多年后,这个隐藏许久的真相才被揭开。
在自然条件下,炭疽是通过致病源的炭疽杆菌芽孢(属于细菌的一种内生孢子)来进行传播的,当炭疽杆菌芽孢经由皮肤、消化系统或呼吸系统进入人体内时,就会引发致命的炭疽病。
炭疽芽孢具有极其恐怖的传播性(具体介绍下面再说),在生化实验室中研发的炭疽武器,为了充分利用空气传播性,会将其制作成了一种类似于气溶胶的细密粉末。
炭疽粉末的制造其实和酿酒异曲同工:将它们放在巨大的发酵桶中培养,配合以适当的条件,很快繁殖力惊人的炭疽就会充满整个发酵桶。随后,炭疽必须进行分离和干燥处理,并最终制造成粉末状。
在19区生化实验基地制造炭疽武器的过程中,将这种恐怖的生命体和外界阻隔的关键,就是干燥机排气管上的那一道过滤器。
1979年3月30日,星期五那天,基地的一名工作人员发现通风管道有堵塞的情况。于是他将干燥机关闭后,去除了填塞其中的过滤器,并进行清洗维护。他按照规定留下了书面的通知记录,然而他那马虎的上级主管尼古拉中校,却忘了将这个重要的细节添加到生产日志中去……
于是,轮岗之后的下一班主管在日记中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下令重启机器,继续工作。
虽然几个小时之后,就有工作人员发现过滤器被遗忘在了外面,并立刻进行了重新安装,但是,大祸已然酿成了……
最终,陶瓷厂工人成为最先染病的对象,当天工作的工人大多数都患病了,一个星期之内,许多病人就陆续死亡,根据前苏联原生化部门副主任,肯·阿里贝克(Ken Alibek)的说法,至少有105人在此次生化泄露事件中丧生,而确切的数字则是未知的,毕竟所有医院记录和其他证据,都被克格勃销毁了。
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解体前夕,肯·阿里贝克叛逃到了美国,并在那里成为生化领域的顾问,参与了美国政府制定的生化防卫战略中。1999年,阿里贝克写了一本书,专门记录了当年的这起泄露事件,书的名字就叫做——《生化危机》(Biohazard)。
在书中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第19号营地一座忙碌的生化武器制造厂,工人们必须轮岗工作,为苏联军队生产一种干燥的粉末状炭疽武器。这的确是项充满压力和危险的工作,发酵的炭疽菌必须从液体基中分离出来,研磨成粉末,以便在弹头爆炸时形成气溶胶。惨剧发生后,虽然政府尽最大努力进行了城市清洁,大量的消毒剂被喷洒在道路、建筑和树木上,但依然有很多市民都感染了炭疽病菌,产生了许多例炭疽皮肤病。
因此,人们也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泄露事件称为“生化版切尔诺贝利事件”。
03
大家听过埃博拉病毒和朊毒体这样的恐怖玩意,但是炭疽比其它们来,恐怖程度完全不逊色。正是因为炭疽杆菌的一些特性,它们比前两者更加适合制造成生物武器。
上文里也说了,炭疽病(anthrax)是以炭疽杆菌的芽孢作为传播媒介,它的得名来源于古希腊语中的“炭(anthrakos)”,这是因为当它接触皮肤后,会留下黑炭一般的焦黑色水泡,周围还会产生肿胀(鉴于图片比较那啥就不放了……)。
除了皮肤传染之外,炭疽病还可以通过呼吸道和消化系统传入,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了……
所有传播渠道中,呼吸道传播是最可怕的:一旦炭疽芽孢通过呼吸道进入身体,它会首先潜入淋巴结,并在那里开始大量孵化繁殖……惊人数量的孢子最终会入侵血管,并引发大面积的组织损伤和内出血。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呼吸道感染的炭疽病致死率高达85%(噢,即便得到治疗致死率也达到45%……)
作为一种古老的,人畜共患的疾病,炭疽病早在古巴比伦时期就被发现了,在西方的《圣经》和我国的《黄帝内经》中均有所记载,是一种恐怖的瘟疫。1607年,中欧就有6万人死于炭疽病,俄国更是炭疽肆虐,仅1875年就有10万只牲畜死于炭疽病,因此炭疽病又被称为“西伯利亚病”。
炭疽杆菌的芽孢拥有相当强大的生存能力,很多普通的灭活方式都对它无效,无论用消毒剂浸泡,还是加温180摄氏度两分钟以内,都无法有效杀死炭疽孢子。甚至埋藏于地底的炭疽芽孢,依然可以存活数百年之久。
比如中世纪苏格兰医院废墟上的考古挖掘中,就发现了炭疽芽孢,以及几百年前用来杀死它们的石灰残骸,谁都没有想到,重见天日的这些古老孢子竟然复活了。
除了传染渠道多样,生存能力强大之外,传播能力超强也是炭疽可以成为生化武器的重要原因。
每一克的炭疽杆菌粉末中,含有超过1万亿个炭疽芽孢,如果在一座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的上风处,沿着一条长2公里长的线路喷洒112磅炭疽芽孢,最终可致使12.5万人染病,9.5万人死亡。当然了,牲畜和野生动物也无法幸免。炭疽所向,一片死寂。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就在1917年使用炭疽芽孢感染协约国军队的战马和军人。二战时就更不用说了,除了残忍到不择手段的日本人,美国、英国也都研发过自家的炭疽武器。
1942年,英国人选择了苏格兰高地附近一座名叫格林纳德(Gruinard)的无人荒岛,在岛上用围栏围住了上百只绵羊,并通过飞机投弹和爆炸的方式,在岛上进行大规模炭疽武器实验。仅仅三天之后,绵羊就开始大规模死亡,岛上到处都留下它们浑身流血的尸体。
虽然科研人员立刻对尸体进行的焚烧和掩埋处理,但在30多年之后的1979年,对岛上土壤的采样显示,每克土壤中依然存活着3000到45000个炭疽芽孢。最后,英国人只能用近300吨甲醛杀毒液洒满了岛上每一寸土地,才算解除了生化危机。只不过,这座岛至今仍然是荒芜的无人岛。
二战之后,大家几乎已经忘记了炭疽的恐怖,直到2001年9月,人们才重新想起这种曾经人人闻之而色变的存在。
9月18号那一天,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和纽约邮报等美国新闻媒体办公室都收到了一封可疑的来信。三周之后,两名民主党参议院也收到了类似的信件(感兴趣的可以放大看信纸上写的啥……)。
当他们打开信封后,发现信纸上还有一些非常细密的浅褐色粉末。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不起眼的灰尘一般的存在,居然是死神附体——武器级的炭疽芽孢粉末。很快,22人出现炭疽感染症状,其中11人更是将炭疽芽孢直接吸入。最终,五人死于这次恐怖的炭疽袭击。
那么,这些信件中的致命炭疽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04
其实,美国人和苏联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炭疽武器的可怕,因此1969年时,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就下令终止炭疽武器的研发。三年之后,苏联人也同意结束研发,双方共同签署了著名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Biological Weapons Convention),两边都信誓旦旦地宣称会停止生化武器的开发。
然而事实证明,所谓条约不过是一些幌子。
美国人以研究生化武器防御为借口,光明正大地建立了政府生物防御实验室,继续研究炭疽武器。
没想到的是,2001年那次生化袭击中,他们就尝到了恶果:那几封信件中的炭疽杆菌全部属于同一菌株——安姆斯菌株。而这个菌株,最早就是在马里兰州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这家机构还研究过雷斯顿埃博拉病毒)的政府生物防御实验室中开发的。
当FBI调查过程中,隶属于这家生物防御实验室的员工布鲁斯·爱德华兹·艾文斯(Bruce Edwards Ivins)扛不住了,选择服毒自杀,他也是这起案件中唯一确定的嫌犯。
而苏联人呢,他们虽然明里不敢继续研究,但仍然悄摸摸地在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炭疽泄露事件就是他们领到的教训。只不过他们当时死皮赖脸不认账,硬说是食用污染的肉所致,直到1991年叶利钦上台后才勉强承认。
可惜的是,苏联人当年并没有立刻吸取教训。
1971年时,一群前苏联渔业科学家搭乘一艘名为雷夫·博格号(Lev Berg)的科考船,来到中亚咸海中一座名叫沃兹罗日杰尼耶(Vozrozhdeniya)的无人岛附近时考察当地水质时,因为小岛复杂的地形而迷了路。
博格号驶入了小岛深处,并在这里忽然遭遇了一团诡异的褐色烟雾。
当船只从烟雾中离开时,一名年轻的女科学家开始剧烈地咳嗽。
几天后,她开始出现发高烧38.9℃,头痛,肌肉酸痛的症状,并在就医后检查出她感染了天花,并立刻服用了抗生素和阿司匹林。虽然这位女科学家早前就接种过天花疫苗,但她的背部、面部和头皮上仍然长出了大片的皮疹。
因为治疗及时,这位女科学家幸运地逃过一死,但另外9名感染者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其中有三人死亡,包括她的弟弟。
一年之后,又有人发现小岛附近漂浮着两具当地渔民的尸体。在此之后,这座岛周围又出现了大量死亡的鱼类。根据附近渔民的说法,后来还有两个探险的户外爱好者上了岛之后,就再也没能回来……
显然,岛上存在着什么致命的东西,让一起敢于接近它的生物,全都死于非命。
05
从外表上看,这座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小岛,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但是,通过中情局的机密航拍照片,可以看到这座岛上不但有码头,有渔民工作的木棚,还有一些类似于靶场和兵营的建筑。
更诡异的是,岛上还有数量可观的动物围栏,和一些看似科研机构的建筑……
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英国的那座死亡之岛——格林纳德。
事实上,这座与世隔绝且长期以来几乎无人知晓的小岛,很早就被苏联人看中了。1948年时,他们在这座岛上,建立了一个绝密的生物武器实验室。这做实验室隶属于一个被称为Aralsk-7的高度机密项目,整个项目的最终任务只有一个:规模化生产生物武器。
因此,女科学家应该值得庆幸,1971年她只是遭遇了天花感染,更恐怖的东西,要到几年后才会降临岛上。
1979年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炭疽泄露事件爆发后,苏联人并没有舍得销毁那些他们苦心研究的宝贝。而是将大量的炭疽芽孢混合在抑制其生长的漂白剂中,并成批地转移到了沃兹罗日杰尼耶岛上。
据估计,最终转移到岛上的炭疽芽孢,竟然有100至200吨之多……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剧毒之物大量扩散出来,显然威胁性绝对远远超越切尔诺贝利事件。当年,这些炭疽芽孢被放置在岛上一个叫做坎特贝克(Kantubek)的小镇附近。说是小镇,其实就是当年的实验基地和住宅区。
在这座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前苏联机密基地里,不仅存放有炭疽杆菌和天花病毒,还有伯纳特氏立克次体、土拉弗朗西斯杆菌、猪布鲁氏杆菌、普氏立克次体、鼠疫耶尔森氏杆菌、肉毒杆菌毒素和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等多种生物武器。
更不可思议的是,这里曾经还是一个集幼儿园、中小学、游乐场于一体的小社会(简直有种《辐射》背景的感觉)。
更恐怖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里的科研人员便开始大批撤离,他们留下了大量未经妥善处理的生化武器,并在此后的多年里数次泄露,最终让这座小岛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剧毒之岛。
2001年时,一批穿着严密的防护服的美国科学家,来到沃兹罗日杰尼耶岛上进行生化危害考察。
此时的岛上已经是一片荒芜,曾经的实验室已然只剩下断壁残垣,曾经用来饲养豚鼠、仓鼠和兔子的数百个笼子散落得到处都是。从实验室遗迹里的那些熔化的试管和培养皿就能看出,苏联人离开时显然放了一把大火,想把一切都焚毁。
生化实验基地两公里开外的露天试验场,是用来测试生化炸弹的有效范围和扩散速度的。旷野里时不时有老鼠和昆虫出没,小队成员全都小心翼翼地躲开它们。理论上而言,生命力强悍的它们,如今也是病毒和细菌的绝佳载体。
如今虽然除了小队成员岛上空无一人,但谁都不敢掉以轻心,毕竟这里四下潜伏着比人类更加可怕的生命体。
通过一番调查,这帮冒险家吃惊地发现,因为岛上的植被稀疏,加上沙漠气候的炎热天气(夏季温度可达60℃),大部分病毒和微生物都被杀死了。但是,依然还有一个唯一的例外,你们都想象得到的:炭疽。
由于某些区域有炭疽的存在,仅仅十五分钟后,队员的防毒面罩过滤器就开始报警:呼吸器的滤芯已经饱和,不能再使用了……
考察队员决定当天就离开沃兹罗日杰尼耶岛,在临行前,一名队员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的笔记:岛上的污染状况比想象中好很多,如果能够进行一次彻底的消毒喷洒,也许可以消除危险。希望这座“重生之岛(岛名的意思就是rebirth)”上,炭疽永不重生。
是的,当人类费尽心思制造这些毁灭性的武器时,或许最先被毁灭的,就是我们自己。
我的绣球花是咋了?
绣球花养护起来,很容易出现脱水的问题,题主的这棵绣球,叶子边缘出现脱水的现象,如果此时盆土已经完全干透了,考虑可能是干旱导致的,因为青山盆浇水有个问题,那就是一浇水,水就很快顺着盆子的侧壁开孔流走了,很容易土球内部还没有湿透呢,长期就会造成植物脱水,虽然此时看起来盆土表面还是湿的,因此我建议首先排除干旱的可能性,因此青山盆浇水,一般我都是连续浇2-3次才能保证盆土完全湿透。
除了干旱造成的叶子边缘干枯,过分的潮湿、积水,也会造成根系腐烂,此时仍然会出现根系的损伤,根系损伤以后无法吸收水分,也会造成叶子边缘的干枯、焦边等问题,因此建议排除一下是否存在积水的可能。
第三,造成根系损伤,可能还有肥害,比如突然大量施肥、水溶肥浓度太高、喷洒的叶面肥太浓,也会造成根系损伤、叶子脱水的问题,因此肥害的可能是也是比较大的,建议排除这方面的问题。
当然病害也会出现叶子焦边的可能,比如菌害往往是从叶子边缘的气孔趁虚而入,也会造成病害,不过我自己养护绣球花,往往病害是造成叶子上有褐色的斑块或者斑点,一般不容易出现这种焦边的可能,倒是月季容易出现这样的炭疽病症状。
其次绣球如果整个夏季养护都没问题,到了秋天变成这样,也可能是光照不足、通风不好引起的,因为秋天光照比夏天要弱很多,绣球到了秋天开始旺盛的生长,此时没有逐渐增加光照、改善通风,反而继续喷水,容易造成叶子光合作用不足、湿度大,从而引起病害。
所以我的考虑是,可能是盆土没有浇透导致的,其次建议喷洒一点杀菌剂,然后逐渐增加光照,慢慢的过度到全日照管理。
都是玉痕平时种花的经验,觉得有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呗!
请各位大佬指点下?
很高兴和友友们一起来探讨养花的心得,非常乐意回答友友提出的问题。从友友发的图片看应是兰花,兰花在我看来是高大上的花卉,更是许多花友最爱养的花草之一,同时也是比较难养的花卉,用花友们的话讲太“娇气”。因为动不动就容易出现病害,有时候花友无法对自己兰花病害进行判断和治疗,那个头疼啊非常理解,有时候眼巴巴地看着它慢慢枯萎。
一、让我们先来加深一下“花中君子”“王者之香”兰花的映像
兰花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外形上它的花瓣是对称的,有六个花被,其中一个化成唇被。它的花粉呈团状,更利于它的授粉。花朵比较小花茎笔直,叶片常见于翠绿色、浓绿色,叶片上的角质层厚度不同,比较特别。
兰花被誉为“花中君子”、“王者之香”。在中国传统四君子梅、兰、竹、菊中,和梅的孤绝、菊的风霜、竹的气节不同,兰花象征了一个民族的内敛风华。因此对于兰花,中国人可以说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感情与性格认同
二、兰花容易出现的几种病害
在养护兰花过程中最常见的几种病害症状有:生理性焦尖症状;褐斑病症状;炭疽病症状;黑斑病症状;叶枯病症状;枯尖病症状;叶枯病叶上又患黑斑病;炭疽病、黑斑病同时危害;病叶交界处的黑色横纹;生理性焦尖、褐斑病、炭疽病、枯尖病、叶枯病和黑斑病综合症状等病害症状。
三、褐斑病症状的针对性预防和治疗。
根据友友的图片看兰花应是褐斑病症状。叶片病斑长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赤褐色,边缘红褐色。病斑多发生在叶缘,叶两面着生灰色霉状颗粒。多与圆斑病、黑斑病同时发生,只是危害的部位、病斑形状与大小不同。
防治方法:做好清洁工作。用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800-1000倍液,80%代森锰锌可湿性剂800倍液,40%百可得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10%世高3000倍液。
黄皮果成熟时出现干枯果是什么病因?
栽培管理当中,会因为多种因素造成黄皮果的干枯现象,一旦发生这种现象是很难治疗的,这些现象的产生是由于品种原因,肥水原因,温度原因,病害原因,各种因素引起的这种现象,所以要及时的预防。
品种原因:由于水分,空气等环境的影响,地区差别,种子表现就会有很大的差别,某些地区表现良好的品种,如果换地区栽培的话表现就会不一样,所以要选择在本地区产量,高品质,好抗病毒等表现良好的品种作为当家品种来培养。
肥水原因:在肥水营养供应充足,植株徒长严重的状况下,通风不良的地块发生黄皮果的现象是最为严重的,氮肥施用量偏多,钾肥使用量不足的地块儿也会特别严重,所以要根据不同生长发育阶段需肥的特点,合理进行施肥。
温度原因:
生长发育适宜温度适合在25到28℃,夜间是12到15℃,在转红的阶段,温度要超过32℃,黄素形成会受到抑制,就会出现这种现象,落果时,在转红阶段,金8℃以下低温冷害的话,就会造成生理紊乱,被破坏,即使温度调节到适宜的温度,也不会变红,容易形成这种现象。
病害原因:多种病害也能够引起黄米果现象的发生,例如叶霉病,病毒病,害虫,螨虫,斑潜蝇等等。
注意肥水管理和整枝:可以根据不同实际的需肥规律来施肥,做过之前可以适当多施氮肥来促进植株的生长,坐果之后多施钾肥来促进果实的发育,喷施甲克素和复合微肥6000倍的爱多收,可以提高植株的抗性,减少黄皮果的发生,结果期内棚里不要土壤太干燥了,以见干见湿为宜,如果植株枝叶生长太茂盛的话,可以适当的剪掉部分叶片。
黄皮果是一种良性的水果,里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等多种微量元素。黄皮果中的铜是人体健康不可缺少的微量营养素,对于血液,中枢神经和免疫系统,头发,皮肤以及各种组织有重要的影响。科学家最近在西伯利亚永久冻土中发现46000年的鸟类尸体?
越来越多的古生物科学家把目光瞄向了永久冻土层,希望在永久冻土层中找到一两个保存完好的生物遗骸,以便开展科学研究。
我们知道,生物死亡后,遗骸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会被分解,分解后的物质重新流回土壤供植被吸收。但是微生物的分解需要一定的条件,那就是需要合适的温度,当外界温度较冷时,微生物分解的效率会变慢,甚至完全停止工作。
人类利用这个现象,制作了冰箱,将一些易腐烂的物体存放在其中,延缓腐烂的速度。
在地球上,冰川和永久冻土层就是这样天然的冰箱,当生物在此地死亡后,由于气温较低,微生物分解速度变慢,因此生物的遗骸可以在此保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时甚至能达上万年,甚至上百万年。
目前,科学家们已经从永久冻土层中挖掘到了1.2万年前的幼犬,2.8万年前的猛犸象,4.2万年前的小马驹。
最近科学家又从永久冻土层中挖掘到了一具4.6万年前的鸟类遗骸,经测量确定,该鸟类为一只古老的雌性角百灵鸟。
作者介绍说,通过它的遗骸,科学家们可以研究灭绝动物的行为,还可以根据它的生活习性,来确定当时的气候,研究当地的生态环境变迁。
然而,该生物遗体的发掘,也引起另一部分科学家的担忧,因为生物遗骸身上很可能潜藏着4.2万年前的病毒或者细菌。随着人类的挖掘,该生物体内的病毒和细菌很可能会重新在生物界流通。
冻土层之下的病毒事实上,科学家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知道,在100年前,导致欧洲人口约5亿人感染的西班牙大流感,在人类世界中已经消失了100年。然而传染病专家居然在阿拉斯加永久冻土层中一个流感患者的遗骸上找到了该病毒。
这意味着这种病毒并未从地球上消失,只是潜伏在永久冻土层中。
无独有偶,加拿大一个科研小组也在新墨西哥州的山洞里,发现了一种细菌,这种细菌已经与世隔绝了400多万年。
这意味着,无论是病毒还是细菌,都可以在严酷的环境中长久生存,直到遇到下一次适宜的环境。
一般情况下,永久冻土层中虽然存在着病毒,但由于土壤被冰封,所以这些病毒并不会被散播出来。然而这些年来随着全球气温变暖,一些永久冻土层开始解冻,病毒随着被解冻的水流汇聚到河流之中,此时该病毒就有感染生物的可能。
除了全球变暖之外,挖掘猛犸象牙的商人也有可能导致病毒进入生物链。
我们知道,为了保护大象,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禁止了象牙贸易,然而猛犸象牙却没有被禁售。
而且,猛犸象生活的地区刚好处于高纬度地区,气温较低,死亡后遗骸不易孵化。因此永久冻土层中有许多猛犸象遗骸,许多人通过挖掘猛犸象牙来替代象牙,高价出售。
商人在挖掘猛犸象时,并不会注重对环境的保护,而是会破坏永久冻土层,导致微生物以及病毒从永久冻土层中解放出来,并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重新回归到生物圈。
重生的病毒其实人类每天要面临大量的病毒,但大多数病毒都不会感染人类,这是因为病毒想要感染人类,需要与人类细胞的蛋白质相对应,如果不能那么病毒就不能进入人体细胞。
大多数病毒都不能与人类细胞的蛋白质相对应,所以这些病毒无法感染人类。但是该病毒此时不能感染人类,不代表永远不会感染人类,要知道它们的基因变异速度非常快,再加上繁殖周期短,造成病毒很容易就变异。
变异虽然没有方向,但架不住瞎猫碰到死耗子,一旦该病毒变异出能够感染人,如果此时人类又刚好接触到了它,那么就会导致人类生病。
如果该病毒在传染人之后,还具有非常高的传染性,那么人类社会就会爆发流行疾病。
也就是说,冰川之下的病毒虽然不一定会感染人,但是对人类以及自然界有潜在的威胁,为了消除威胁,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永久冻土层不被破坏。
然而即使没有挖掘猛犸象的商人,永久冻土层也正在被解冻,究其原因还是我们常说的全球变暖。
一旦永久冻土层完全解冻了,可想而知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