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花双共夫txt全文,作为他的邻居娶她前妻合适吗?
邻居家的大哥离婚了。然后你要取他的前妻?这件事我听起来,感觉有一点怪怪的。
那么你大哥离婚,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到现在我都搞不懂,你和他的前妻,是否之前就已经心存的暧昧或者做出一些出格的事,还是相互之间都看好对方。然后最终被你大哥看见。然后无法忍受你们两个之间的这种,不正常的关系而选择离婚。把机会留给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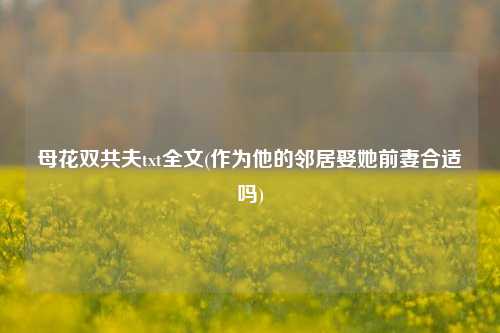
但是我就想,假设你和他前妻结合了,那你之后怎样面对你这个大哥呢?
对于你这位邻居大哥,他又会怎么想。你这位邻居小弟,居然把他的前妻给娶走了呢?
我想这件事,你应该认认真真前前后后,仔细想一想你们结婚之后所面对的问题。最后只能是劝你,认真处理好此事祝你幸福。
最火的电影和电视剧有哪些?
2020年上线了非常多的好看的电影,但是很多视频网站都是收费看的,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免费看这些电影的方法
2020上线的电影比如《匹诺曹2020》《喋血战士》《野性的呼唤》《回家之路》等等
这些电影现在只要是智能电视用户,就可以免费看啦,高清免费无广告,这就需要安装一个叫“快来看”的软件,这款软件里所有海外大片全部都是第一时间更新,而且免费看
除了最新的电影,“快来看”还有非常多的美剧,韩剧,以及日剧可以看
快来看现在已经上线各大电视应用市场,可以在沙发管家,当贝商店,欢视助手,欢视商店,还有TCL,长虹电视的官方商店搜索下载
女性是如何相处的?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了,我便认认真真的回答你。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历史上的一夫多妻制,并非只是简单的“一位丈夫娶很多个妻子”,而是充斥着各种约束与礼数,甚至因为复杂的时代背景,而具备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
今天就让我们来捋一捋古时的一夫多妻制,尽量从多个角度,带大家剖析历史的真相。纵观古史,伴随礼法与律令的多方面发展,在我国古代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制”始终据核心地位,即一位古代男性配偶再多,同时也可能拥有很多“妾”,但真正意义上的“妻”,只有一位。
在现代很多人的眼中,能娶很多妾,或许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然而在古人看来,妻与妾这二者之间,其实存有本质上的区别,妾的地位低于妻,通常用于称呼地位贫贱者,最早如《周礼》中所说:
臣妾,男女贫贱者。男奴称之为“臣”,女奴称之为“妾”。当时提起臣或妾,总是会带有些许贬义,如《周书。费誓》中提到:马牛其风,臣妾通逃。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左传》中更是直言:男为人臣,女为人妾。——《左传·信公十七年》此处的“臣妾”,含有“臣服”的意思,而非我们所广泛认知的“大臣官员”,另外《战国策》中也有明确提到:
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战国策·秦四》由此可见,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贫贱者的代名词,而得不到世人对于其身份,以及社会地位的认可,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妾的社会地位得不到认可,甚至一度作为奴隶的代名词而被广泛使用,那么为何后续又会成为家庭关系中的一员呢?
这个问题最早也是可以追溯到西周,虽然礼法中明确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但并不意味着当时的男子只能拥有一名配偶,实际上则是赋予了男性拥有多位配偶的权利,但同时又对“妻”的地位与权利予以保护。
关于一位古代男性拥有多位配偶的现象,最早在西周盛行过一种(ying)妾制",虽然“腾妄”也被称作“妄”,但实际上“朦妾”的身份要比妾高出一些,且能够随主人出席正式场合,也有正式身份,所以“腾妾制”也被看作是最早的“多妻制"现象。
古代人出于多子多福的考量和男性征服欲下,一夫多妻制自春秋战国时期便开始形成固定。
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度,在汉人的历史上实际上遵照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和妾有着严格的界限和地位差别。像《红楼梦》中,妾称为“姨娘”,光看赵姨娘如何对婆子抱怨便知道她和王夫人待遇有多大的差别。
大户人家的小姐嫁到另一个大户人家是做妻,买来的或者家生丫头是妾。妾可以随意更换甚至送人或者卖出。因为家世背景的差别,导致了妻和妾社会地位的根本差异,又因为封建社会森严的家长和等级制度,所以一般情况下妻妾相争的情况不会出现,妾普遍对家长主母忍让和服从,主母也一般不会为了和妾争风吃醋而自己降低身份。
我们知道妾的地位比丫头好不了多少,丫头与丫头怎么相处,说起来就应该更偏向于今天的“同事”关系。大家都是丫头,地位摆在那里,能改变的程度并不多,能争一争的,也就是男人的宠爱了。
一般来讲,受宠的小妾得到的物质回报当然丰厚一些,小妾们各凭姿色或者才情从男人那里获得宠爱和物质条件。不过很多时候,就算获得了财产也只能在家中内部流转,是不能带走的。
就好比今天的同事关系,大家竞争的也就是升职加薪的机会,公司是属于老板和老板娘的。而且小妾并没有晋升机制,所以只有加薪机会没有升职机会,这样看来,相处起来比今天的同事还要和谐很多呢。
事实上也是如此,同为大家庭最低下的阶层,相互之间如果不是直接的利益冲突一般会平静相处。作成密友互相帮扶的例子还是很多的。
所以,电视剧里面那种妻妾斗争基本上不会出现,更不会有男人为了小妾反过来打压妻子,和妻子反目。在那样的封建制度下,社会等级森严,男人也不像今天一样脑子里会有什么人人平等的思想,所以他们会很乐意的左拥右抱又不用给予太多,尤其是名分。
不过,任何事都有例外,史书上记载的悍妒事迹也不少,有妻子怒骂、反目甚至将妾置于死地,也有男人特立独行宠妾灭妻,不过这就像村女嫁给了高干子弟一样,发生的概率很低,和主流社会并不相符。而且大户人家尤其在意家风建设,一举一动都恪守礼教约束。
就像末代皇帝赙仪的妃子文绣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的,别人都以为皇宫里的妃子会斗得很凶,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各自待在自己的寝殿里过自己的生活,互不干扰。像外界的评说或者小说戏曲之类的,只不过是外面看不见的人凭空想象和猜测罢了。
为何说萧红在小说中展现了一幅幅女性的受难图?
开宗明义,萧红在短短的一生中所经受的情感磨难,本身就是一部动人的小说。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似乎从不专注于对两性关系以及女性命运的集中刻画,对她来说,更加关注的是女性生命本身存在状态的苦难和灾难。
我将结合具体作品,说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01《王阿嫂的死》虽然意在暴露地主的狠毒残忍,王大哥被地主活活烧死,小环的母亲被地主的儿子侮辱后气愤而死,而王阿嫂的死更是由于地主踢了一脚而动了胎气的缘故,但直接导致王阿嫂死亡的却是女人万劫难逃的自然刑罚——王阿嫂是难产而死。
不管人们是如何痛恨地主的凶狠,然而面对王阿嫂生产时血淋淋的场面,人们唏嘘感叹的只能是作为女性的在劫难逃的命运。
如果说萧红在《王阿嫂的死》中对女人难逃自然法则的揭示还仅仅是一种无意的流露,那么到了《生死场》,萧红则强化了女性所受到的肉体折磨以及男人施与女人的暴虐,比如成业的婶婶就对和金枝相好的成业说:
“等你娶过来,她会变样,她不和原来一样,她的脸是青白色,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会打骂她呀!……”“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萧红对此早有所悟,她看到父亲不仅对她、对仆人、对祖父没有好面孔,就是对新娶来的母亲也是:
“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萧红在想:
“母亲也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她终于明白在那样的社会里,女人所处的卑下的地位。因而,我们就不难理解在萧红笔下的女性的深重的苦难。当金枝未婚先孕时:
“肚子变成个可怕的怪物”,“她把肚子按得那样紧,仿佛肚子里面跳动了!……“她的心立刻发呕一般颤嗦起来,她被恐怖把握着了。”而在《弃儿》中,怀孕、生产给女人身心带来的痛苦折磨更是历历在目。然而,当女人为两人的原始冲动带来的后果惊恐万状痛苦万分时,男人却“完全不关心”,只是一味地任由本能驱使着,当女人恐怖地迎来“刑罚的日子”,以生命作着抵押,男人非但不体恤女人,反倒拳脚相加。
比如,书中五姑姑的姐姐生产时险些丧命,但她的丈夫却“每年是这样,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并且“一点声音不许她哼叫”,似乎生产是女人的罪过。在痛苦和屈辱这双重折磨下:
“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脚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在这里,萧红终于无法抑制自己对男性自私无情的愤恨,并借《生死场》中的金枝之口说出:
“男人是炎凉的人类”这一让人震惊的认识。
《生死场》话剧剧照
耐人寻味的是,萧红在描述女人们受到刑罚的同时,笔锋一转,以“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正在生小猪”让人产生类比联想,揭示了“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生存境况,暗示着女人动物般可怜的命运和无法自主的人生轨迹。
例如,当金枝为躲避日军的奸淫而逃到城里时,她反而没有逃脱被自己的同胞污辱的命运,她羞恨地再次回到了乡村。当王婆劝她再次逃往城里时,金枝愤然地说:
“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后一句话,实际上在金枝身上正透露出萧红把自己仅仅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份对男性进行了无情批判和深深谴责。
金枝固然万分痛恨小日本子,因为是小日本子使她抛下重病的母背井并离乡。她以把自己弄得又脏又丑而躲过了小日本子的凌辱,但她却无力逃脱同胞男性的侮辱。
这正是金枝同时也是萧红的悲愤所在,金枝终于被男人逼得走投无路,出家做了尼姑,而这正是女性逃离男性世界的唯一选择,然而尼姑庵已空无一人,世上再没有女人的容身之处。在这里,萧红所展示的是男性世界对女性生命的欺侮和摧残以及萧红的愤恨和无奈。
虽然萧红在她的小说创作中没有露出她极富戏剧性的曲折和多难的感情、婚姻生活的痕迹。但是,她已经把她在个人情感生活中的感情、思考和认识融入作品当中,以完全不同于个人生活经历的人物事件传达了她在两性关系中的情感体验和切身感受。
萧红曾经历了一个女人所能遭受到的太多的苦难:告贷无门、流浪街头、孤立无助、被男人欺骗、始乱终弃,在困顿中经历两次生产的痛苦,胎儿一个送人、一个死掉给身心留下无法弥补的创痛,疾病缠身,感情受挫,婚姻不幸,所有这一切都让萧红对男性既有依附的无奈,更有被伤害的痛苦和愤恨。
因此她的朋友池田不只一次地发出惋惜、不平的感慨:
“进步作家的她,为什么另一方面又那么比男性柔弱,一古脑儿被男性所支配呢?”其实,萧红何尝不想像一只大鹏金翅鸟一样在天空展翅翱翔,然而她“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她说:
“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元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这种矛盾一直困扰着萧红的一生,她婚恋的不幸,她与异性世界说不尽、理还乱的恩恩怨怨,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一道道阴郁的影子。《生死场》、《呼兰河传》中表现出的对女性苦难的同病相怜,以及对男性施加给女性身心巨大创痛的仇视,便成了萧红在现实生活中情感体验和自身感受的巨大投影。
萧红动笔写《呼兰河传》的时候,身息重病,感情生活面临危机,心境尤其悲凉,因而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对女人的世界,更感到心酸和悲伤。她曾说: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在这里,萧红把自己的遭遇和故乡女性的不幸命运交织在一起来写,引起了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
读《呼兰河传》那水一样流畅的文字时,谁也不会想到这短短的十多万字,她竟然写了三年之久。更不会想到在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里萧红经历了怎样颠沛流离的生活:
感情的剧变、生产的痛苦、婴儿的夭折、婚姻苦果的再次品尝、病弱的体质、不安定的生活、朋友的淡漠疏远、心境的寂寞,萧红就是在这波折的人生境遇中把握住自己的灰色情绪,写出了非同一般的作品。
而且,这期间,整个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七七卢沟桥点起抗战的火焰,不久之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
02这一段时间,也是“女性身份”加剧骚扰萧红的时期,“女人”在萧红眼里始终是一个敏感的字眼,与萧军、端木蕻良的相处也日益让萧红感到作为一个女人的悲凉,男人带给她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但萧红把一切苦痛和怨愤都埋在心底,甚至对她的好友白朗也密而不谈:
“似乎要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一直不要说出口,好像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值得听她的告诉。”萧红在《小城三月》中对翠姨心态的揣摩简直就是萧红自我心境的写照。然而在她其他一些文字里,她曾直接表露出她对男权的讽刺和愤恨,她在介绍欧美两位女作家的作品《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的文章中曾记录了这样一幕情景,当她借来这两本书想重新翻一翻时:
“被他们看见了。用那么苗细的手指彼此传过去,而后又怎样把它放在地板上:‘这就是你们女人的书吗?看一看,它在什么地方?”接下来是他们一系列嘲笑的情形,萧红明白他们不过是开玩笑,但她不解的是:
“为什么常常要取着女子做题材呢?”萧红在这里提到的“他们”就是萧军和端木蕻良。两个个性完全不同的男人在对待女人的态度上达到了惊人的一致,这不能不引起萧红的诧异和深思。
到她创作《呼兰河传》的时候,她对男权的反感更是一目了然,她甚至在描述呼兰河小城几个精神盛举时专门列出一节“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以娘娘庙和老爷庙相比照,集中刻画了男性对女性的欺压,以讽刺的笔法表现了自己对男性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愤恨和蔑视:
“娘娘庙是在北大街上,老爷庙和娘娘庙离不了好远。那些烧香的人,虽特说是求子求孙,是先该向娘娘来烧香的,但是人们都以为阴间也是一样的重男轻女,所以不敢倒反天干。所以都是先到老爷庙去,打过钟,磕过头,好像跪到那里报个到似的,而后才上娘娘庙去。……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悔,就是同类也不同情。比方女子去拜过了娘娘庙,也不过向娘娘讨子讨孙。讨完了就出来了,其余的并没有什么尊敬的意思。觉得子孙娘娘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子而已。只是她的孩子多了一些,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这里,萧红以近于调侃嘻笑的语气揶揄笑骂,对男性欺侮女性的行为和根由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似乎在不经意间道破了事实的真相。同时,以她独特而敏锐的感受对老爷庙和娘娘庙进行了全新的诠释,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萧红在《生死场》里写到王婆、金枝等女人的愚昧、懦弱时还写了她们性格中积极、觉醒的一面。赵三组织了“镰刀会”反对地主加地租,而王婆非但没有像李二婶子那样害怕惹火烧身加以阻挠,反而弄了一只枪来,并暗中协助他们,她表现出来的这种沉着冷静以及胆量甚至令“镰刀会”的领导者、她的丈夫赵三感到可以敬重。
赵三误把小偷的腿打断进了监狱,又由于东家的帮忙而从监狱放了回来,从此赵三对东家感恩戴德,再没有了反抗之心,地租到底加成了。王婆面对失去了英气的丈夫,连她“后脑上的小发卷也像生着气”:
“我没见过这样的汉子,起初看来还像一块铁,后来越看越是一堆泥了!”王婆有着连大男子也不如的豪侠英武之气。金技虽然没有王婆那样鲜明的阶级、民族的爱憎意识,但她对男人的认识却是清醒的,男人的种种恶行让她得出了“男人是炎凉的人类”的结论,并对男性世界不再抱任何幻想与此相比。
《呼兰河传》中的女性却显得麻木无知得多,她们同小说中那些男人一样完全认同于既定的现实,对现实的一切都没有丝毫的异议,更没有丝毫的抗议。她们对一切都逆来顺受,甚至认为那是理所应当本该如此的。
比如,老胡家的大孙子媳妇挨了丈夫的打,她并不像金技那样产生怨恨,而是说:
“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于是便“心满意足地并不以为那是缺陷了。”女人就这样毫无怨言地认同了男人指派给女人的角色,并自觉自愿地以男性的标准实现自身价值。她们身受男人的欺压不仅无动于衷,还常常充当男性代言人严格监督规范着女性同伴,其手段的残忍狠毒与男性相比无不过之。
尤其可悲的是她们对自己同类相残的行为并不自知,她们对所谓的“规矩”深信不疑,毫不动摇。
如老胡家小团圆媳妇所遭受的种种虐待,大半是身为女性的婆婆施与的,而她的婆婆并不以为那是虐待,而是完全出自“好心”,要把小团圆媳妇“规矩成一个好人”来,以至不惜付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代价。
她们的愚顽毫无感觉足以证实她们被传统男权文化浸染毒害之深,巳经达到了令人体目惊心的程度,而好好的一个小姑娘就命丧在她们这些男权文化的执法者的“善举”之下,实在让人痛心疾首。
最后萧红让死后的小团圆媳妇变成了一只很大的流着眼泪哭泣的白兔,使所有读过这个故事的人对无辜的受害者生出无限怜惜之意。
萧红的敏锐和深刻还表现在她生动地刻画了那些帮闲人物。正是周三奶奶、杨老太太、东家的二姨、西家的三婶这些“心慈”的女人为传统男性文化充当了助封为虐的帮凶,与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们一道共同促成了小团圆媳妇的死亡。
03萧红对地笔下的女性不仅仅是“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她不仅谴责这个死气沉闷的落后城镇和愚昧落后的人群,对不幸者寄托着不可遏止的同情,更对女性世界的污浊予以嘲弄。
在萧红眼中,正是女性自身的自卑自轻自贱使得女性纵容和协助他人为自己掘下了深不可测难见天日的坑穴。这为萧红的小说在思想内涵上获得了历史的纵深感。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曾在小说里塑造了遭受多重压迫的农村妇女形象,在鲁迅笔下她们不仅受封建四权的压迫,同时自身的愚昧也是不能觉醒的原因。萧红显然承继了鲁迅的深刻思想,而且更具批判意识。
她没有把农村女性作为美和纯洁至善的化身来歌颂,更没有写出农村妇女生命意识、个性意识的觉醒。
相反,萧红刻意凸出的仍是那些认命麻木地接受苦难、把一切现状当做合理现实的女性,在她们身上没有丝毫觉醒与反抗的亮色,相反却起着维护传统制度和一切陈规陋俗的作用。
在萧红的作品中很少看见王婆、金枝那样刚烈而颇具个性意识的女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萧红女性意识的衰弱,相反,萧红正是通过对这些毫不觉醒的女性浑浑噩噩情状的关注,表现了对女性自身愚昧的批判意识以及对女性命运的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深刻思考。
萧红在她的小说中用了大量生动的笔墨描写了众多的女性,如金枝、王婆、麻面婆、五云嫂、老胡家的两个儿媳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回避了男性作家通常塑造的恶魔与天使的女性形象,尤其回避了具有所谓传统美德的理想而完美的女性化身,而是剥开那层披在女性身上的美丽外衣,让女性恢复她们的本来面目,回到她们的原生状态。
在萧红那里,既没有疯狂、神秘的疯女人形象,也没有温顺贤淑、富有牺牲精神的传统女性,萧红似乎无意于抨击或赞美某种女性形象,或者更无意于对女性予以道德评判,尽管在《呼兰河传》中她透露出对王大姑娘这一不拘“规矩”,敢于坦然面对自己的真挚情感和人们的非议的欣赏,但那完全不同于男性笔下的理想女性。
事实上,萧红更在意的是女性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女性与男性之间那种亲密又冲突的若即若离的关系。
《生死场》话剧剧照
《生死场》中金枝、福发的女人、五姑姑的姐姐的处境就再显明不过地告诉人们,女性作为性对象和生产工具的悲剧命运。当金枝受着青春的蛊惑与成业不断地约会时,恐惧、痛苦的种子也就播在金枝的身上,如她所写的:
“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即便是在本能的冲动中,女性也像一只落人虎口的猎物任由男性蹂躏摆布,当成业带着姑娘走下高粱地时“像猎犬带着捕捉物似的”,而共尝禁果之后,男性了无牵挂一身轻松,而女性却开始独自品尝两人酿下的苦酒。
当金枝的身心都受到怀孕的折磨时,成业却“完全不关心”,只顾野兽一样重复着本能的驱使。“妇人们的刑罚”很快就要降临到金枝身上了,而金枝也渐渐“和别的村妇一样……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了,她们开始诅咒男人,就连“性情不会抱怨”的麻面婆一到了生孩子时,也会大声怨恨男人。
在萧红那里,很难找到形容女人的美丽的词句,相反,无论是:
“瘦得象一条龙……鼓着肚子,涨开肺叶般的哭她的手撕着衣裳,她的牙齿在咬着嘴唇她和一匹吼叫的狮子一样”,“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的王阿嫂,还是那有着因为染布而变得“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手的木讷愚笨的王亚明。萧红笔下很少出现过娇艳妖冶或者温婉贤静的女性形象,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萧红常把女人比作各种愚笨弱小的动物。
如常把迟钝傻气的麻面婆比作“一只母熊”或“在柴堆上耍得疲乏了”的“狗”、“微点的爬虫”,而不断地述说命运的王婆却被比作“猫头鹰”或一只“灰色的大鸟”。
金枝更在男人和暴怒的母亲面前,“和小鸡一般”、“小鼠一般”;或者一个“捕捉物”,而生产时“光着身子的女人”,却“一条鱼似的”,“爬在那里”。
当五姑姑的姐姐在产婆的劝勉下勉强站起来时,“她的腿颤颤得可怜,患着病的马一般,倒了下来”,“只有女人在乡村夏季更贫瘦,和耕种的马一般。”,“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这种血腥的场面完全是对以往女性形象所赋予的任何诗意的消解。
同对感人故事的回避一样,在这些惨烈的意象背后,潜藏着萧红刻意追求的对女性悲怜处境的真实描摹。
《生死场》中那个“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是唯一一个萧红在这篇小说中正面描写的美丽女性,她是“如此温和,从不听她高声笑过,或是高声吵嚷,生就的一对多情的眼睛,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到绵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美丽温柔的女人,从一出场就褪去了美丽的光彩,患上了瘫病,整整一年:
“坐在炕的当心”,“没能倒下睡过”,每夜她都发出“惨厉的哭声”和“哼声”,“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变绿,整齐的一排前齿也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像一头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宛如一个人和一个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关联。”打鱼村这个曾经是最美丽的女人终是死了,葬在荒山下。萧红以这个美丽女人的毁灭再次向人们宣告,完美的女性根本就不存在,而理想的女性人生也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已。
萧红以这诸多“血淋淋的现实”击碎了女性身上被赋予的光环,还原了女性在历史与现实中的生存状态,突破了以往作家笔下常常出现的“天使”与“恶魔”的两极形象,生动再现了在传统宗法乡村社会环境里女性的真实处境和本来面目,以敏锐的笔触展现了一幅幅女性受难图。
回答完毕。
有没有一些好看的名人回忆录?
推荐一个搞笑的台湾名人吹牛回忆录↓【前台湾水军大都督黎玉玺】回忆录所列战绩比纳尔逊还牛,大陆网友送其外号铁嘴水上漂
前台湾水军大都督黎玉玺☞人称铁嘴水上漂
黎玉玺(1914—2003),字薪传,四川达州人。前台湾海军总司令、台湾驻土耳其大使,与王多年(金门防卫司令陆军总司令)并列为台蒋时期的陆海军“福将”。
黎铁嘴通篇自吹自擂的回忆录
黎玉玺回忆录出版后,因其战绩吹牛过份(比纳尔逊还牛),在内地网络上引起一片嘲讽,人送外号:“ 铁嘴水上漂”。
据其回忆录称“1946年月到1947年11月,率舰在渤海、辽东一带巡弋,搜攻中共船艇。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一共共俘获解放军轮船和机帆船七艘、击毁敌五十吨至千吨级机动轮船七十五艘,帆船数百艘,使敌之海上交通陷于中断”
“此外,1946年9月,率舰在庙岛附近发现共军炮艇三艘,最大者约二百吨。亲冒矢石奋勇杀敌,敌三艘炮艇二沉一翻,全军尽墨”。(这事奇怪之极,共军46年就有上百艘轮船炮艇了?)
除了自称在截断共军海上交通线方面战功累累以外,还自称多次参加支援陆军作战,以其三吋舰炮屡创“奇迹”。。。。。1946年9月21日,配合陆军整编第八旅扫荡龙口。“永泰”舰以主副炮猛烈轰击敌军炮兵阵地。数日后接获情报,炮击时炮弹均落街内,房屋大部破坏。
10月5日,参加攻击威海。“永泰”舰之三吋大炮射击至为精准,每三发就有两发径射入敌之钢筋水泥机枪工事射口,可谓百发百中。海军司令桂永清将军闻报后大为惊喜,特自旗舰发电嘉奖”。
“10月6日,奉命驰援营口。“永泰舰”以炽烈炮火支援陆军。共军在海上火力打击下伤亡惨重,突入之敌几尽全歼,共被击毙第三师师长黄子祥以下二千余人,第一师师长与炮兵团长负重伤”。(这个第三师师长黄子祥是谁?解放军军中是有个黄子祥,陕北红军出来的,也确是师一级军官,但是1949年他还在陕北任职,似乎不太可能会死在营口)。
到1948年8月,黎铁嘴调升“太康”舰舰长。奉命率舰参加锦州-葫芦岛作战,支援陆军十七兵团侯镜如部进攻塔山。
在黎舰长的指挥下:“太康舰的三座三吋主炮大显神威。炮击共军打鱼山阵地时,在九千码距离上弹无虚发。共军伤亡惨重,据说曾有一个整排被太康舰的一发炮弹炸得尸骨无存”(隔着那么远又怎么知道一发炮弹炸翻共军一个排?)
黎玉玺官运亨通,据说有一段故事:1949年春,蒋介石撤台前,曾经搭乘太康舰在上海附近指挥作战,当时的舰长正是黎玉玺。期间蒋每一次有事要找舰长时,黎舰长都会回答一句:“玉玺在。”老蒋当时正是下野之身,闻听此言自然大觉吉利,自此黎玉玺便官运亨通。在林遵起义之后,他便于1949年5月2日接任第2舰队司令一职务。
据其回忆录称,生平最敬仰者,惟英国海军名将霍雷肖·纳尔逊勋爵一人尔,“而他的战绩也不比纳尔逊差”, 据其回忆录所列:
1、民国四十四年(1954)二月十八日,台山列岛海战大捷。击沉共军大型炮艇6、登陆舰8、武装机帆船8。另据空军报,击沉共军潜艇一。
2、民国四十七(1958)年六月十九日-二十二日,在闽江口击沉共军鱼雷艇6艘。
3、民国四十七(1958)年金门八二四海战。达成运送八英吋巨炮任务(轰雷行动),为该海战关键人物之一,击沉共军鱼雷艇10艘、击伤5艘,俘获共军3名。(解放军此战一共出动6艘鱼雷艇,以战沉一艘的代价击沉对方一艘4000吨的补给舰)
4、民国四十七(1958)年金门九二海战。击沉共军鱼雷快艇3艘、大型炮艇8艘,击伤敌炮艇2艘,是为台山列岛大捷后的又一次空前大捷。仅以上四战合计,被击沉的的共军舰艇即在50艘以上。再加上数年间的无数次小规模交战,黎一生击沉的共军舰艇当在百艘之上。
1959年2月,在台升任海军总司令。




